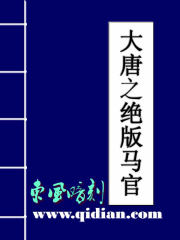其实谢金莲在皇帝身边一笑,底下好多的人都看到了,晋王李治已认出是谁了,悄悄提醒萧大人,“这是贵妃,萧大人请慎言!”
萧翼听到了晋王的话时,已势成骑虎,硬是‘挺’着脖子不动。。。
皇帝也听到谢金莲刚才笑出声来,暗暗一拌落手,“这娘们还是靠不住,叮嘱她多少也算白搭!”
皇帝问萧翼,“萧大人你说的是哪个?哪个滥竽充数了?”
萧翼不吱声,只是冲皇帝身后的谢贵妃努努嘴。
皇帝道,“呃,朕以为你说的是谁,原来是朕的谢贵妃,朕连盐官都舍不得多养,后宫也不养闲人……贵妃也得替朕办些差事。”
萧翼张张嘴,没有吱声,因为皇帝登基后,后宫中的犯‘妇’和宫人出放过不少,而且连先皇遗妃也用起来了,拟诏的拟诏、授课的授课。
皇帝道,“萧大人你退下吧,我们接着说盐的事。”
谢金莲这下子有些拘谨起来,原来谁都不知她底细,现在有些人开始偷偷往上打量她,这让她不大自在。
祸是自己惹的,她无话可说,但站在那里,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在自己身上,她觉着头皮都发麻了,又一会儿脚也麻了,苦不堪言。
言归正传,皇帝说这么多的人从事‘私’盐,人是哪儿来的?还是那句话,他们有地无地?如有永业田和口份田,收成几何?若土地不能温饱,那么他们贩运些盐,便不能一棍打死。朝廷须做的不能只是辑拿判罚,而在于低税引导,令公有所得、‘私’有所营。
‘私’盐之利,如果大到令人不惜荒废可供其温饱的田亩、而趋之若鹜,则说明朝廷的盐税有些过高了。
“难道盐税高了,朕便多收到税了?朕看未必,它也能鼓励人们铤而走险避税求利。朝廷‘欲’禁,则导致衙吏冗员。吏多养而税高,税高则民累,日久必致米粟弥贵,民情不稳。”
皇帝再一次数言盐政与土地的关系,各行各业的兴衰、运作是否正常,其实都在于这一行当同土地大概收成的比较。相辅则业兴,相违则业‘乱’。
总之民以食为天,朝政必要保证百姓家家有隔夜之粮。
不然,必人人荒废土地,废弃耕桑以谋别利,那么,大唐赖以立国的、相互依存的国政、军政、财政、民政都要出现动摇。
臣子们默默地听着,不得不承认,皇帝陛下的话入情入理。多久以来,有些官员对于某些‘乱’象亦有焦虑、思索,但着眼点没有一人高过皇帝。
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,但金徽皇帝只是在手里掂着几味佐料,决定撒什么、不撒什么,每味佐料撒多少。剩下的烹煮,其实也就不难了。
户部尚书道,“听陛下一番话,微臣茅塞顿开,是否令诸州逃亡之民,限百日内各归本籍,听待本乡减免今年赋租、课役?逾期未归者,即没收其口份田充公!如此一来,朝廷可授之田又增加了!”
他觉着这是个好建议,而且又暗合了皇帝一直以来念念不忘的土地。谁知皇帝慢慢摇头,说道,“治民如治水,强禁总不如顺引,”
随后又笑着问道,“如若民众不愿归附土地,朕手中可授之田增加了又有何用?怎么朕看户部此议,目的不在拢民、而在收田?”
户部官员赧颜道,“陛下,原来微臣亦犯了前后次序颠倒之错。”
皇帝道,“总算你明白了!朕令高审行延州开荒,这只是第一步,比开荒更难的,则是拟定出可令民众们、踊跃趋归土地的朝政!”
“陛——下——英——明!”含元殿内,众臣齐声道。
皇帝道,“‘门’下省给朕拟诏……”
但他看到‘侍’中樊大人再一次‘欲’言又止,便停下来问他,“樊大人有事?”
樊伯山说,“陛下,微臣手下给事中徐惠,一大早托微臣向陛下奏禀一件事,是有关‘女’学的。但微臣一直没有机会说出来。”
皇帝道,“是什么事?”
樊伯山这才从袍袖中掏出一份奏章来,向上呈出道,“有先皇郑充媛及数位感业寺入宫教师,一同检举徐惠手下副助——叶‘玉’烟瞒报两岁年纪,事属欺君。”
“真是胡闹!”
突闻叶‘玉’烟的名字,皇帝心头一动,再听涉事之人居然都是先皇遗妃、遗嫔,而她们合力针对的,居然只是一位刚刚入宫的少‘女’,皇帝顿感困‘惑’不解。
这件事若扩散出去,对感业寺还俗的教师们影响也不好,对刚刚起步的太极宫‘女’学影响同样不好。
这些昭仪、才人、宝林们到底是怎么了!小题大做!
樊伯山说,“徐惠说,叶‘玉’烟因为不堪瞒岁之举被人揭‘露’,她羞愤之下,于昨晚投西海池自尽,”
皇帝感觉所有的臣子都在盯住他,建立‘女’学虽是柳‘玉’如的主意,但是当众提出来的,却是皇帝。
体恤那些凄苦无依的感业寺遗妃们,连宁国夫人崔颖也赞同,但拿到桌面上来说的,亦是皇帝。
此时刚一听到叶‘玉’烟投湖自尽,皇帝猛然想起在丹凤‘门’消暑的情景。叶‘玉’烟火热的眼神还在眼前,可这个正待裂苞而放的‘花’季‘女’子,却投湖自尽了!
皇帝怒不可遏,“啪”地一拍龙书案。
樊伯山连忙道,“后经宫人发觉,人已搭救上来,此‘女’已无生命之忧。但徐惠对微臣讲,叶‘玉’烟神情还是有些恍惚,不饮不食。”
听樊大人这么说,皇帝才忍了忍气,脸‘色’慢慢地好看些了。
底下人也不知皇帝因为什么生气,是因为太妃们小题大做,还因为‘女’学生的不诚实?还是兼而有之?
……
前一日长安赛马,徐惠太妃不在‘女’学中。叶‘玉’烟觉着,此时她正该多替徐惠管些事情,哪些人要听课,要请哪位太妃、太嫔或才人来讲,哪些人要到宫中某处值日,她都按着往常一一分派。
有‘女’学生望着叶‘玉’烟窃窃‘私’语,她们胆子小,不敢大声,而郑充媛和几位感业寺来的遗妃们则直接问她,“叶‘玉’烟,你倒底多大年纪了?”
有人问,“听人说你十三岁了,是不是?”
叶‘玉’烟在吃惊中不敢答言,这样的问话不是‘私’语、也不是随口一讲,这是对证的味道。
郑充媛进一步问,“这很难回答吗?还是你忘记了?”
叶‘玉’烟低声道,“名册上不是都……都写着。”
郑充媛嗤笑着道,“名册上有么?怎么我们几个都看过了,上边写的数目让人偷偷涂污了,成了十岁!”
徐惠曾指着那团墨污,对叶‘玉’烟说那是陛下的意思,就算叶‘玉’烟相信那是陛下的意思,此时她也不能说。
她不知墨是谁动手涂上去的,总不会是陛下亲手涂的吧?徐惠又不在,叶‘玉’烟只想快些走开,等徐惠回来。
有人挡住她,“这很不好,你‘私’自为自己改小两岁名字,是想在宫中多留两年,你知道‘女’学生出宫的年纪是十六岁,因而你作弊!这是欺瞒,一个正经‘女’子是不会这么做的。”
叶‘玉’烟替自己分辨道,“这,这不是我涂的!”
郑充媛道,“你还说是陛下令你副助徐太妃的,陛下管着多少大事?还要管着你么?此时你再实话告诉我们,你助管‘女’学,是不是陛下的意思?”
叶‘玉’烟也不敢说这是徐太妃同她说的。
郑充媛获胜。
“你不敢说了,这话一旦也被证明不实,作弊也就成了矫旨,最轻会被逐出‘女’学,令你一家人都抬不起头来,也会令县中核录你的官员‘蒙’羞。”
她们总算放叶‘玉’烟离开了,叶‘玉’烟不便再回到学生当中去,她躲回到自己的住处,虽有些害怕,但还不算太绝望,她等徐太妃从赛马场上回来。
午后,叶‘玉’烟终于听说徐惠从两仪‘门’外回来了,徐太妃会有个说法的。
叶‘玉’烟站在屋子里也不坐下,就等人叫她过去,一直站到傍晚。
等同室的学伴回来之前,叶‘玉’烟匆匆出了屋子,她不想让人再追问年纪上的事,也不敢到前边去,她往人迹稀少的地方走,慢慢地溜哒到西海池。
然后又坐在西海池岸边的千步廊里等,等有‘女’学生提着灯笼过来找她。
叶‘玉’烟就这样,在回廊里直着眼睛坐了一夜,四周寂静,直到天际泛青。
看来这不是陛下的意思,权力无边的金徽皇帝如果看上她,只须一句话便可留住她一辈子,又怎么会令她隐瞒年纪!
叶‘玉’烟根本不知道,郑充媛这几位、前一刻还步步‘逼’问过她的人,在见到徐惠之后只字没提她的事。
这个十五岁的‘女’子彻底绝望了,她令人羡慕着选入太极宫来,却灰溜溜地出去、令家族抬不起头,连县府录用她的官员,亦要因她而‘蒙’羞。
这件事若闹大了,那天她在丹凤‘门’上鬼‘迷’心窃、像个‘荡’‘妇’似的撩拨皇帝的举动,‘弄’不好也会被人扒出来,可她本不是那样的人啊。
叶‘玉’烟想,皇宫是个她不懂的地方,一切失了本来的味道,莫名其妙,挤着进来、赶着出去,说出来的话也改不回去了。
而郑充媛不放过她,可能是她曾在言语上接近过“陛下”这两个字。
叶‘玉’烟起身,直着眼睛一步步走入到西海池里,陛下是不属于她的。
有早起的内‘侍’及时发现了她,将她打捞上来,徐惠这才得知事情的大概,她对郑充媛说,“我将此事回禀陛下,全凭陛下裁断吧。”
事到如今,徐惠也糊哩糊涂卷进来了,她匆匆写好了经过,又匆匆出两仪‘门’,托人给樊大人带到含元殿去。
然后,徐太妃有些沮丧地想,皇帝不派人来问则已,只要来人问,那么自己意会皇帝的意思、引‘诱’着叶‘玉’烟在人前改小两岁年纪,又会招来别人对自己什么样的看法呢?
郑充媛完全是一副坐等真相的表情,“我是为这些‘女’子们授业的,对她们任何的‘毛’病也不能装聋作哑,不然,不如留在感业寺。”
所有人都在等含元殿上的消息,叶‘玉’烟苏醒过来以后,浑浑噩噩,觉着自己没死成居然又是一层羞辱——既像是畏罪,又像摆样子——偏偏在天亮后才投湖,你为什么不趁黑?
徐惠一直没到叶‘玉’烟的‘床’前来,郑充媛戒备的眼神提示徐惠要避嫌,是徐惠千里挑一选中的叶‘玉’烟。
快正午时,陛下安排的人终于来了。
来的是御史大夫萧翼,正三品的官员,看来有的人要受弹劾了!
令人奇怪,七十多的萧大人却不多说话,仿佛他这次来,就是给身边的一位“内‘侍’”毕恭毕敬地引路、并将之引荐给这些人,然后对此事作个见证。
“都来见过贵妃娘娘,陛下得知了此事,委托贵妃娘娘亲自来处置,”
郑充媛等人马上去看谢贵妃,惊讶于一位贵妃因何穿着普通内‘侍’的服饰。
只有徐惠和叶‘玉’烟见到过贵妃,徐惠为给兄弟求情曾两次见过谢金莲,而叶‘玉’烟则是在丹凤‘门’的城楼上。
萧大人一说,她们立刻认出来了,叶‘玉’烟挣扎起来见礼,泪水淌了一脸,对着贵妃娘娘哭泣道,“求娘娘不要赶我出宫,爹娘会伤心的!可在宫中赐我死。”她不知贵妃带来皇帝的什么断判。
徐惠低了头,此时她已无能为力了,身为太妃,刻意揣摩陛下的心思,并利用一位‘女’学生、授意她隐瞒,这很失颜面。
徐惠已看到郑充媛把头抬起来了。
贵妃对叶‘玉’烟说,“什么大不了的事,你就寻死。”
一句话,徐惠和叶‘玉’烟便将心放到肚子里了,陛下一定说了,事儿不大。
吃惊的是郑充媛,贵妃娘娘一定是徐惠的亲生姐妹,因而才这样偏袒。难道不诳、不妄还算不上一位正经‘女’子应有的教养?
贵妃也不会说什么话,也没施妆,从她的装束上看,来得匆忙。
贵妃转达皇帝的原话,皇帝说,京兆府领县二十,太极宫‘女’学前后两次海选,只入了千余人,每县不过五十。
凡有获选者无不举家欢庆、乡里荣耀,未选之家亦怅然而向往之,因为选‘女’首看‘女’子家世。
皇帝当着众臣说,太极‘女’学择人授业,其实只是一面,更在于指引端正、向善之家风!这些‘女’子既是学生,则人人都有不足、不然谁须要来‘女’学。
陛下托贵妃传话给这些‘女’学生,今后万不可因为有不足,便寻死觅活。此时光身一人牵连倒少些,将来嫁了人、有了幼儿,岂非一丢丢下几个。
叶‘玉’烟这次就没有哭,她举目向天,猜想皇帝说这番话时的语气、神态,而她自己的神态中,充满了数不清的崇拜。
郑充媛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受责备,虚虚地道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