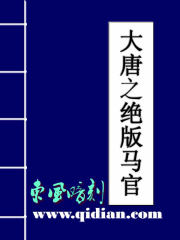柳玉如飞快地看那几页证言,内容太多了,她直接翻到后边,发现画押的人里面有好几个人都是到高府里来过的,其中还有她十分熟悉的一个名字。
但是她没时间细看了,瞥见陈令史此时已经心满意足地靠在墙上、再次眯起了眼睛。她牢牢地拉住了那几页纸,另一手摁着卷背,把它们从几道细麻绳子的束缚中拉了出来,纸张只发出了轻微的声音。
她看看令史没有反应,将它们折起来,无声地揣到贴身的地方,然后再往下看。
“群臣争进言,‘君集之罪,天地所不容,请诛之以明大法。’陛下语君集道,‘与公长诀矣,从今而后,但见公遗像耳!’……斩满门于四达之衢、籍没其家资。君集临刑,容色不改,谓监刑柴将军绍堂道:‘君集岂会反乎!然尝为将,破灭二国,颇有微功。请为我言于陛下,乞活一子、一妇,以守祭祀。”
柴绍堂问,“公有两子,欲活哪个,我必为公言。”
侯将军沉默……“无双独子而身弱……我如何放心!不如随我去吧!到了地下也好与夫人共抚之……请活峻!柳氏无辜,我已愧对其父数年。悔一时之怯懦、而致每日之鞭笞!辗转不能寐、抚心不能平,生莫如死……请活柳氏!则君集虽死、犹解脱也!”
柳玉如猛地一下抽噎,吓得谢金莲赶忙伸出袖子替她遮掩。因为柳玉如长久地死死盯了这一段话、两大滴泪珠落在上边晕染开来。谢金莲也看清了这一段儿,这便是他最后的话、最后的情景,好像发生在眼前。
幸好陈令史并未睁开眼睛。
两个人匆忙擦擦眼睛,发现眼圈儿红红的。她们生怕陈令史突然醒过来,想起在西州的家中时,高峻曾经让她们互舔眼皮。于是不须商量、牵了手,彼此去舔对方的眼皮。
好半天心情平复下来,她们不忘小心合上案卷,再把它个罗列起来。又静了一会儿,发现门外的天色已经渐渐暗了。谢金莲对陈令史道,“陈大人……”
“喔、喔,两位夫人,可看好了?”
他发现那位下午来的美貌夫人始终不说话,眼睛看着门外。又是谢金莲说,“多谢陈大人,我们看好了!”
两个人一前一后从史馆中出来,一到大门外,没人,柳玉如又抽噎起来。
樊莺听到两人的脚步声,已经跳下车子,她见到柳姐姐如此伤心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再看谢金莲反倒比她好一些。
车帘撩起、放下,蹄声响起,车子缓缓起动。
月上柳梢头,再过半个时辰各坊间的门就要关闭了。趁着大好的光景,街边有许多人在。甚至在一处空场上还围着一群人,正听一位说书的先生朗声说故事,声音远远地传入车中:
“秦王愁道,‘敌营重垒,如何得之?’众将挠头、皆以为难办。这时,有小矬子侯君集应声而出,对秦王道,‘蹿房越脊、夜行取物这有何难,待我去去就回!必定轻松得手尔!’……”
马车内,柳玉如猛地挣扎起来,就要去掀车帘,被樊莺和谢金莲死死抱住,发现她浑身颤抖、几乎不能自控,哽咽道,“这、这才几年的功夫!”马车飞快地驰了过去。
远处,传来一片叫好之声,“看爷赏!!!”,一片叮叮当当铜钱落盘的声音。
不远处,马车在一片绿柳下面停住,柳玉如不再挣扎,只是平静地对谢金莲和樊莺道,“妹妹,你们说峻要是在这里,会不会放过他?”
樊莺道,“姐姐,算了,他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,不说些奇怪的,让他怎么活呢!”又道,“我猜师兄听到了便不会让车子驰过来,当时就跳下去了。如果他处在我们这里,便停都不会停的。”
谢金莲道,“侯将军是不会与他计较的。”
柳玉如道,“有理,我们走。”马车再次驶出去。
此时在车子里一片昏蒙,谢金莲想起自己看到的卷宗上的那段话,眼泪就止不住流了下来。原来她只是从崔氏初到牧场村时,从崔氏的口中知道柳玉如曾经是侯公府的夫人。
自那以后,她一直认为,柳玉如新婚之初便把自己拉到家里来,一定是出于这个原因——同病相怜——她们都与一个男人有扯不断的关系。
现在,谢金莲又知道了高峻的身份,原来与柳姐姐从侯公府的浩劫之中一起逃出来的,就是高峻。
三个人一进高府大门,看到大门口停着一顶轿子、候着四名轿夫,还有一匹马、两名护卫。此时阁老亲自送出两个人来,柳玉如偷眼一看,正是前些天到府上来的通直散骑常侍褚遂良。
在他的身边跟着一位珠光宝气的中年女子,应该是他的夫人。几个人看到从门外匆匆走进来的三人,两个是尚食局差役的打扮,一个是一身的胡服。
褚大人驻足,笑着道,“三位别驾夫人好兴致!嗯,这倒是个好办法!”他指的是柳玉如和谢金莲两人身上的衣服。
大门处红灯一片眩眼,阁老先前只是认出了樊莺。闻声定睛一看,也认出了柳玉如和谢金莲两个,他一愣,但很快就掩饰下轻微的不快,对他们道,“见过褚大人和褚夫人……”
自己家里的晚辈孙媳,在长安城里公然穿了公事服行走,这在行事一向谨慎的阁老眼里是看不大惯的。只是他自一见面,对她们几位就是很满意的,不快只是一闪就过去了。
褚夫人笑容可掬地看着她们,却发现只有穿胡服的年轻女子冲自己万福了一下,而两位穿了公事服的人却没有动,反倒是先前行礼的女子见了,礼施到一半也收回去了。
她仔细看了一眼其中一位,虽然不是女装,但一点也不逊色于旁边那个胡服女子,另一个也不错,不过被她们比得有些黯淡。
褚夫人不大在意对方的失礼,只是眼睛仍盯了柳玉如,笑道,“阁老,你虽未明着说她们,已经把她们吓到了!怪可怜的。”
等褚遂良与夫人单独到了街上,再也没有旁人时,夫人低声对他道,“怎我看其中一个有些面熟呢,好像在哪里见到过,一时又想不起来了。”
褚遂良道,“夫人是在画中曾见吧?哈哈。”
行至半途,褚夫人忽然撩开了轿帘儿,对着丈夫招手。褚遂良把马并过去,听他夫人说,“我想到了!那年……命妇们一同进宫朝见……她那个板着脸、却让人恨不起来的娇俏模样我忘不了的。”
褚大人低声道,“夫人不得胡讲!西州别驾的夫人,还到不了命妇的行列。再说,她们丈夫如日中天,你别多事。”
夫人仍是将信将疑,一行人远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