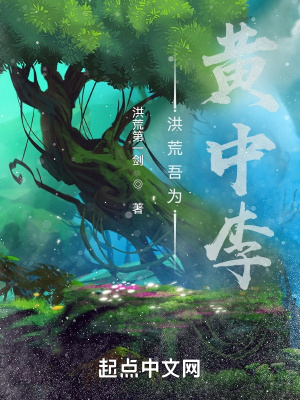墙上无人看守,墙外不见火把,近万铁骑裹足衔环蛰伏于东门外夜雨之中。马儿刨地喷着白气,马背上刀剑出鞘,战卒个个如标枪挺立。只待城门洞开,北燕这支钢铁巨兽便会脱缰而出,兵锋所指,山阳尽血。
太祖以北斗创北燕七军,原有两支战骑闻名遐迩。
一支名为开阳,可惜当年三降城一战,两万开阳铁军已随镇北将军苏仲瑾一起损失殆尽。那一战惨胜,而今开阳残军早已弃番号不用,立苏字旗饮马北疆,誓死戍守燕州。
而燕州,被北燕遗弃已久。
无独有偶,另一支北斗第二,名为天璇的北燕骑军也同样已撤番,那些随燕镇川征战多年,巩固江山社稷的军中老卒尽皆被编进了镇国利器四象营之中。北燕皇帝曾言,四象在、北燕雄,四象营兵精将良、甲厚枪长,此言诚不虚。
陈克重来时提着个脑袋,他见豹校尉殷情举了把油纸伞为殿下左右遮雨,忍不住冷哼一声,挤开人又故意把脑袋扔在他怀里,也不管那豹公子吓得手脚哆嗦,递出一封密信,他道:“殿下,这匪首杨大目说是带了龙骧将军秘信前来投诚,被俺给宰了!”
陈克重行事雷厉风行,何况宰都宰了,燕静姝无奈揭开密信看完,撕成碎末问道:“将军可取了东西?”
陈克重摇头,密信自己不曾看过,这杨大目从密道钻出来倒是带了好几十箱东西,可掀开来看,全是一箱箱石头,耍猴不是?陈克重二话不说便两斧头砸了下去,死得不能再死,哪管人是不是龙骧将军举荐。在他想来,顶多不过是些金银细软,也没在意,杀了人堵上密道便赶紧前来复命,毕竟长公主万万不能有丝毫闪失。
“那罗诚还不开门?”眼见约好的丑时将过,陈克重又问。
豹一抱自从入了王府高居屯骑校尉,那可是秩为比千石的官儿,虽然满打满算手下也就管着千人,可一身金灿灿的盔甲不仅好看,黑灯瞎火还能凑合着当灯使。他擦干净了手脚忧心道:“殿下,那罗诚,不会真安心跟着造反耍咱们玩儿吧?”
燕静姝并不多言,纤手一挥,“攻!”
“好勒!”豹一抱得令,也提着一把斧头一马当先,陈克重瞅着没动,豹校尉黑灯瞎火进了城门洞也没见响动。他把斧头高高举过头顶抡圆了,还不待砸下,便见镶了铁皮的城门吱一声缓缓打开,卖力推门的小厮不管,打头便看见个白衣书生冒雨,拉风骑在一匹劣马上冲自己傻笑。
“锦弟?”
豹一抱一不留神斧头落下砸了马掌,那马猛然前窜,他俯身抓紧缰绳便依哩哇啦独自一人杀进了山阳城,看起来气焰嚣张得紧。
陈克重肃然起敬,冲旁人说,倒是小觑了豹校尉!随后他策马而入,身后蹄声如雷、洪流滚滚。
长公主燕静姝的蟒袍外穿了一身黑衣锁甲,模样说不出的英姿焕发,她打马看着闪身躲在门后的苏家少爷,犹豫片刻,又一剑鞘敲在人脑袋上,“叫你洗马,离姐姐说你胆小,竟吓得跑去无望山当道士都不肯,咋样?苏少爷莫不是寻乐子干起了山匪勾当?苏府满门忠烈,也不嫌给你爹和博山侯丢脸!”
苏锦抹了把脸上雨水,一阵苦笑,“说来话长,那长生殿嫌我根骨奇差死活不肯收,谁知归来半道又被裹挟进了山阳城,饱受屈辱还能活着,那可都是托殿下洪福。”
“贫嘴!还不快撑伞!”
雨势渐大,苏锦拿了那把油纸伞,跟着燕静姝慢慢缀在大军之后,左右都是铁甲护卫,二人无言看着满城杀戮,燕静姝比自己还要镇定,偶有问起,也多是感慨百姓疾苦。
寅时的街面格外干净,四象营从东门入,进进出出杀了好几个来回,但凡存疑之人,尽皆被陈克重砍了头。那些负隅顽抗的江湖草莽,在成千上万的铁蹄之下,顷刻间便成了一堆烂肉,燕静姝不忍又无奈不能左右,因为这,便是父皇要的干净。
第二日天亮,大军又慢慢追着一队疲于奔跑的匪兵去往其余四郡,所过之城,无不是以防范不力、救援不及论处,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吏守将,该杀的杀,该押的押,不过小半月,越州便告平靖。凯旋时,听闻候补的官吏路已经赶了大半。
古越复国终究不过一场春秋大梦,除了一首童谣,什么也留不下。
燕静姝回宫赶往山河殿复命时,父皇听完始末,笑骂道:“那苏家小子滑头,杀了朕的龙骧将军吞了财宝不说,还能得封赏,真滑了天下之大稽。”
燕静姝辩解,“或是凑巧,看着他也没那胆子才对!”
罗诚被人枭首,别说龙椅龙袍,五姓梁氏的罪证翻遍山阳城也没能寻到一件,但这并不耽误父皇灭梁家,寻个理由而已,而今梁氏上下百口,便只剩下东都城里的梁老太公疯疯癫癫府上守灵,此种五姓免死,引人嘘唏。
燕镇川摆手又道:“没胆?丫头还不知道吧,你那王府洗马可不是省油的灯,便是今日进城,又在听风楼里把左相的儿子给打了,这次可算下了死手,那王甫,差点再没喘上气!”
燕静姝闻言哑然。
中兴元年四月,永世王凯旋,本该举国欢庆,风头却被东都城里另一事给抢了去。
这日一众兵将畅饮听风楼,恰逢左相儿子王甫高歌一曲童谣,那博山侯府苏少爷不分青红皂白,撩膀子便揍,可说拳拳到肉,跳楼公子豹一抱劝架之余偷下黑手,同样屡试不爽。
这阵仗,把四象营统领陈克重看得瞠目结舌,光酒水就多喝了十几碗。
左相王佑知不依不饶上门讨理,博山侯拄拐出来时狠狠敲了人两棍子,说:“记得左相现在住的那宅子,以前也是住的前朝丞相,姓甚名谁久了记不清了,但我苏长卿当年,便是在那里亲手勒死的人。”
博山侯还说,那孙子打得好,没死是造化,将士尸骨未寒,岂容纨绔子冷嘲热讽。
这他娘到底谁纨绔?
王佑知不敢跟老侯爷争辩,灰溜溜抬着人走后还刻意补了份重礼。可怜了王公子全身挂彩,估计没几个月又下不得床。
这日,闯完祸的苏少爷把桌上佐酒的几十样小菜每样都吃了点,而后撇下喋喋不休的四翁,独自提着壶酒去了囿己园。
老太公不在,园子里坐着个不修边幅的账房先生,苏锦躬身一礼,道:“先生喜酒,不知香五里的浮糟黄酒,可能喝得惯?”